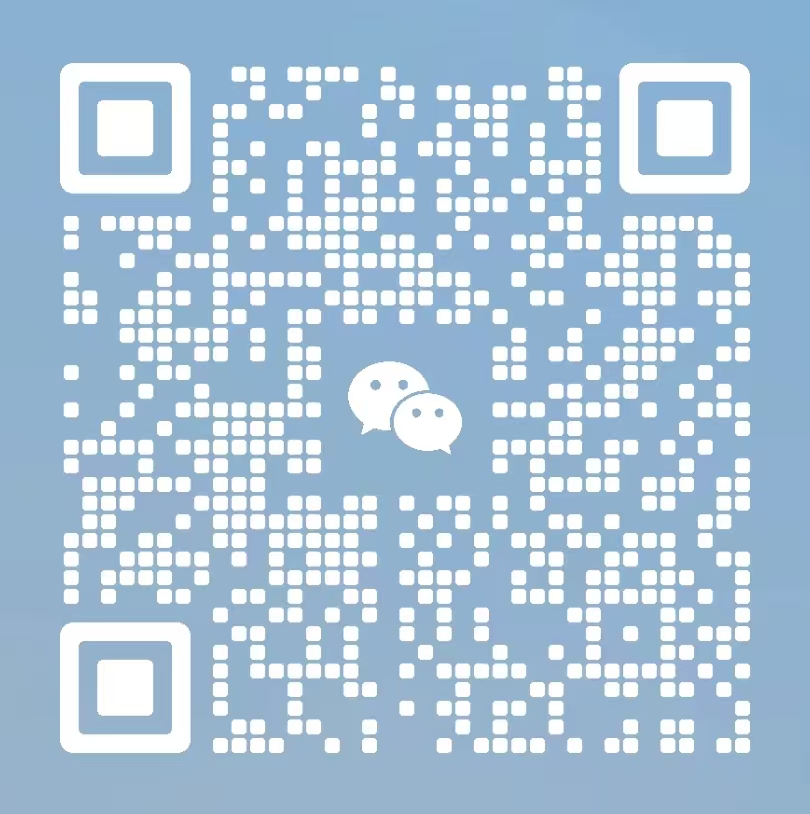关于齐泽克—— 从“做自己”到大他者的凝视
前言
最近有点迷上了齐泽克,某次在某处突然看到的他的独白就被完全击中——“我们以为是现实太残酷,所以要逃到梦境中去,但其实是梦境太残酷,我们只能逃回现实中来。”,。
参考书籍:《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斜目而视》 《基督教的本质》 《介绍丛书:拉康》 以及网络上搜罗来的各种资料。
做自己——终极意识形态诡计
齐泽克说,人戴上面具更接近真实。实际上,我们太期待人们表达真实的自己,这有点适得其反。到头来你会苦恼什么是真实的自己?齐泽克认为,做自己的最好 的方法就是放弃这种幻想。即在我内在的有一个真实的核心,这就是拉康的主体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自己的做事方式,有自己的社会关系,而这背后, 具体的背后,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拉康会说,真相是你就是你的面具,面具背后空无一物,这个空无应对的就是你无意识中被阉割的欲望。表象之下,除了更多的表象 之外,什么都没有。根据其这个意识形态的阐述,当我们以为跳出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恰恰就在终极的意识形态之中。
对于主体性一样,做自己,这就是终极的意识形态诡计。所以那些贩卖梦想的人,售卖的就是这种“做自己”的梦。“做自己”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把戏。虽然也是 对马克思异化的产物,但关键在于,马克思并不认为要寻找异化之前的原初的自我,因为那个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会说,这种真我的概念本身就是虚假的。 在资本主义中,真我变成了被售卖的商品,你越觉得自己被异化,你就越想购买一些商品,找回真的自我,然后越陷越深,进入了成瘾症。让你做自己,基本上就是让你通 过购买商品来呈现自己。所以真我的恐怖之处在于,它是资本主义过剩制度背后的终极幻觉。这种提升和改变真我的想法成为了资本主义售卖的终极商品。而戴上面具 之后,你可以更真实地去扮演被异化的自我理想的形象,而不用担心受到别人的谴责。也就是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自己”时,我们才能有机会去触摸到 那遥不可及的自由感。
其实可以举一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假如世界从一开始就只有我们一个人类(一定程度上的摆脱了大他者的凝视),我们还会去追求作为所谓的“做自己”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现在对世界的一切的认知都是基于社会以及他人的构建,其实也就是所谓的面具构成了我们的意识人格,如果丢掉“面具”,我们什么也不是。正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讲的: 没有表达人的存在的对象,人就什么也不是。(Man is nothing without the objects that express his being. )
诅咒还是馈赠——来自大他者的凝视
齐泽克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个疯子认为自己是一粒玉米,当他被治好并被送回家后,他又回到医生那里惊叫道,我刚刚遇到了一只鸡,我会不会被它吃掉? 医生解释道,你是一个人,不是一粒玉米。疯子回答道,是的,我知道,但是鸡知道吗?对于疯子来说,在未得到鸡的确认之前,它仍然是一粒玉米。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象征效力。 既为了让一件事情为真,我们仅仅知道它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件事情也被鸡(大他者)所知道。例如,在获得某个专业体育机构的承认之前,我并不是一个运动员, 在我的诗集出版之前,我也并不是一个诗人。只有被某种既定的秩序(大他者)所承认,我才是我。否则,即使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玉米,但如果鸡不知道, 那我仍然只是一粒玉米。可能这样的说辞依旧有点抽象,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电视里的被追捕多年的罪犯终于落网,这是在法庭上他们疯狂地忏悔自己的罪行,或者表明悔改之心, 此时我们都能注意到,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们的忏悔。但是为什么他们明知道所有人都不会相信自己的忏悔,但却依旧表明这样的言辞。那他们又是在跟谁说话呢?答案当然是 ,大他者。即便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罪无可赦,只要大他者相信自己纯白无暇,相信自己已知悔改,那么自己就一定是纯洁的。在这里,大他者保证了主体经验的一致性, 提供了生命的终极意义。
齐泽克在他的《享受你的症状》是这样描述大他者的:通过大他者观念的矛盾,我们可以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更为详细地确定同大他者之不一致性的关系当中的 这一罪疚的逻辑。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的话语里,大他者的代理呈现为两种相互排斥的模式: 首先,“大他者”呈现为一个“幕后操纵”的隐秘代理,在舞台背后控制一 切:基督教意识形态中的神圣天意、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商品经济中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历史的客观逻辑”、纳粹主义的“犹太人阴谋 ”......等等。简言之,我们想要实现的东西和我们活动的实际结果之间的距离,结果超出主体意图的剩余,再一次化身为另一个代理,一个元主体(上帝,理性,历史, 犹太人)。对大他者的这一指涉本身当然是根本地模糊的:它可以充当一种让人平静并变得坚强的安慰(对上帝意志的宗教信心;斯大林主义者的信念,即他是历史必然 的一个工具)或一个可怕的妄想狂代理(例如,纳粹意识形态在经济危机、民族耻辱、道德败坏等等的背后认出犹太人的同一只不可见的黑手)。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样一种牺牲的仪式呢?在这里我们要抓住大他者最为关键的【凝视】的功能:不仅主体借由大他者形成稳定的【本质性表象】 ,大他者也在凝视主体,质问着主体的欲望之谜:即你为什么会选择我,而你真正的欲望又是什么,这道凝视在主体身上产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压力,因为主体不清楚自 己的欲望,同时更不清楚大他者的欲望,或者反过来说:大他者的欲望只是主体自身欲望之空无的透射,因此主体只好用【牺牲】来回答所谓大他者的欲望之谜,即牺牲 的逻辑在于牺牲创造出了一个可以由牺牲来满足的大他者形象,通过主体个人的牺牲,大他者能够被生成、产生。同样的逻辑也在强迫症中体现了出来,强迫症患者通过 不断重复强迫行为与强迫思维来充当一种防御,一种对于大他者欲望的防御,而这一系列强迫行为在他们内部的自反馈中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牺牲场景:通过我不情愿地做 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大他者的形象能够被完整地生成出来,我不愿意放弃的本质性表象也能够毫发无损地加以保持。我们在宗教中也能够发现类似的情景,正如拉康 逻辑是:与其让我得知上帝的死亡,不如使我彻底的有罪,主体在这里不愿意牺牲的,自然是【本质性表象】,而其余一切(肉体与束缚与精神的痛苦)皆是可以放弃的。
简单来说各种道德、法律、习俗、社会秩序、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统称为“符号秩序”也就是所谓的“大它者”,它规范着人们,“自我”也栖息在这些东西之上 人的“世界”就是由大他者全盘介入的(大他者始终在场),语言使得前符号的“物”符号化为一个有秩序的、人类可以理解的“世界”。换言之,语言不仅是一个工具,更是 一个“构成性”的中介,没有它,各种“物”将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却不在有一个“世界”。所以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世界”中,由语言构成的符号链就永远包裹着“赤裸的物”, 刨除了一切符号性的坐标(社会关系)我们就无法定位任何对象,即它们“存在”于非符号化的“世界”之外,而不“是”在符号化的“世界”之中。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很难做 到完全拒斥符号秩序,与大他者完全决裂。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拒绝某些微观秩序,例如为了自己的健康,主动选择不喝酒、不抽烟,不用虚伪的欲望满足大他者的凝视。